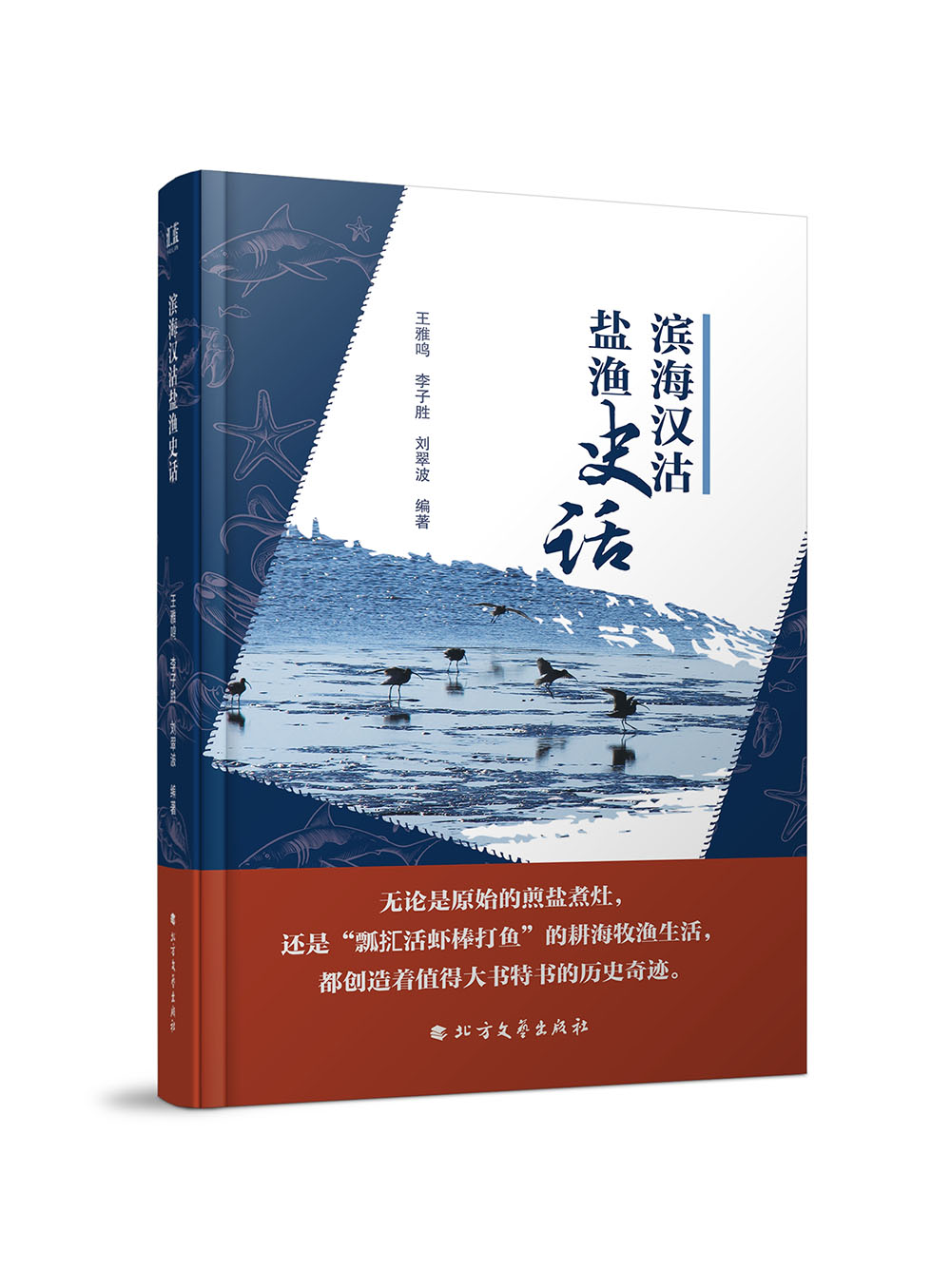李子胜
就像我们对母亲的了解更多的是慈爱、勤劳而对母亲的身世、经历知之甚少一样,我们对家乡的了解也是表象的、甚至片面的,缺乏对家乡历史的深入认知。在很多省市多年前就把古法制盐打造成旅游产品的背景下,滨海新区发展旅游业,绕不开盐业文化的主根脉,作为滨海人,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我们的文化之根——海盐文化。
据史料记载,距今约2500年的春秋时期,汉沽地区的海岸线分布在今日的高庄村、后大坨村、汉沽城区、后沽村一线。距今约2200年秦汉时期,海岸线已在高庄村、双桥子村、寨上镇、茶淀地区一线形成。距今约1300年的唐代时期,海岸又移到汉沽的营城地区以南。今天的海岸线是距今700—500年元代至明初成形。
据《宁河县志》记载:“小盐河,即汉沽也。自潮河(今蓟运河)经汉沽庄北,东达尹家灶、毛家灶、张家码头诸古煎盐处,土缁赤色,锅痕犹存。星相家往往误指为有生气。父老云,潮河即曹孟德凿潞水通泉州渠,以入海者也。汉时,官给盐船自潮河运入,而盐自小河运出,汉无漕运,即潮河亦利运盐耳。”这段记载,反映了公元206年曹操征讨辽西乌桓的战争准备期间,开渠运盐的历史事件。
自古宁汉不分家。宁河与汉沽,无论从方言到民俗习惯,没有清晰的区别。距汉沽十余里的芦台镇,后唐时期形成规模宏大的制盐场——“芦台场”,汉沽、芦台周边区域曾经出土了大量秦、汉及战国时期文物古迹,这充分证明汉沽部分地区在汉代已经成陆,已经有先民再次从事制盐劳作。
在汉代,芦台已成为一个海滨重镇。可以称为北方的扬州。古人有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的诗句,也有“北唐山南保定,不如芦台一五更(读jing)”说法,都是极言海盐业给地方带来的富庶。因煮盐业的发生,芦台也成为了当时的军事重镇和重要商埠。芦台这座千年古镇的发展,除了漕运之便,那就是滨海盐渔之利。
西汉时期,人们用芦苇作为燃料,用大锅取盐碱土,熬制海盐,营城地区和杨家泊区域的大片芦苇,到了深秋,可以任百姓樵采,因为燃料充足,煮盐业因此兴盛。海边煮盐为业的灶户,最初也称海边“炊子”。
进入东汉时期,曹操开凿小盐河,漕运汉沽以及杨家泊地区生产的原盐。小盐河的开凿,标志着汉沽以及汉沽海盐生产的发展已达到一定规模。小盐河是汉沽区域驳盐漕运的主要河道。
地方史的记载,反映了曹操在征讨辽西、乌桓的战争准备期间,曾开凿小盐河,把汉沽东南部盐灶产地的海盐运出来。小盐河这个由海盐和漕运而得名的地区就这样诞生了。“小盐河”改称汉沽,是因为古代人对小河道习惯称之为“沽”,大河道称为“水”。汉沽这一地名,就包含了朝代名称(汉朝)和河道名称(沽水)的双重元素。
芦台与汉沽相距十多里,从近几年来芦台附近出土的大量秦汉及战国时期文物证明,汉沽的杨家泊地区就是古代芦台海盐产地。
五代十国时期,因为战乱,灶户迁徙逃亡,古幽州地区盐业生产停滞,技术断代,贸易中断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这个曾经是古战场的芦台镇出现了盐圣母降临,教人煮盐的方法的各种传说,依据传说,当地人给盐圣母立庙,称“盐母庙”。
盐母娘娘从此成了中国第一个代表盐业的地方神,也开了海盐神话的先河。
到了明代,河流冲击成陆,汉沽地区有了大片的冲积平原,汉沽的其他产盐聚落开始诞生。汉沽地区存有两道贝壳堤。一道是双桥子贝壳堤。即清末时西起李家河子水门,再到双桥子网堡,继续向东至河北省丰南县的涧河村西,长约15公里,宽70~100米,高0.8~1.2米,民国年间已缩短;另一道是蛏头沽贝壳堤,即清末时西起蓟运河河口,向南延伸到青坨子村,再到蛏头沽村东,长约9公里,宽50~60米,高1~1.5米,民国年间已缩短。它是古海岸线典型的标志。
据《长芦汉沽盐志》记载,芦台场煎盐,自后唐同光三年(925年)置场,到清代康煕初年废煎改晒,历800年之久。芦合场煎盐使用铸铁大锅。清顺治十二年(1655年)有锅30面,雍正四年(1726年)减为5面。煎盐首先要制取原料卤水。制取的方法有两种:刮土淋卤及草木灰淋卤。